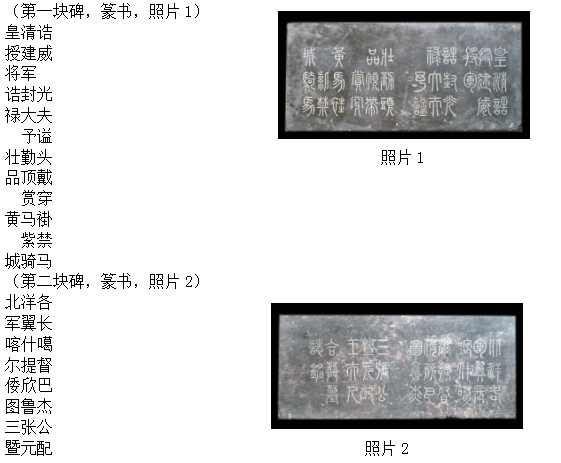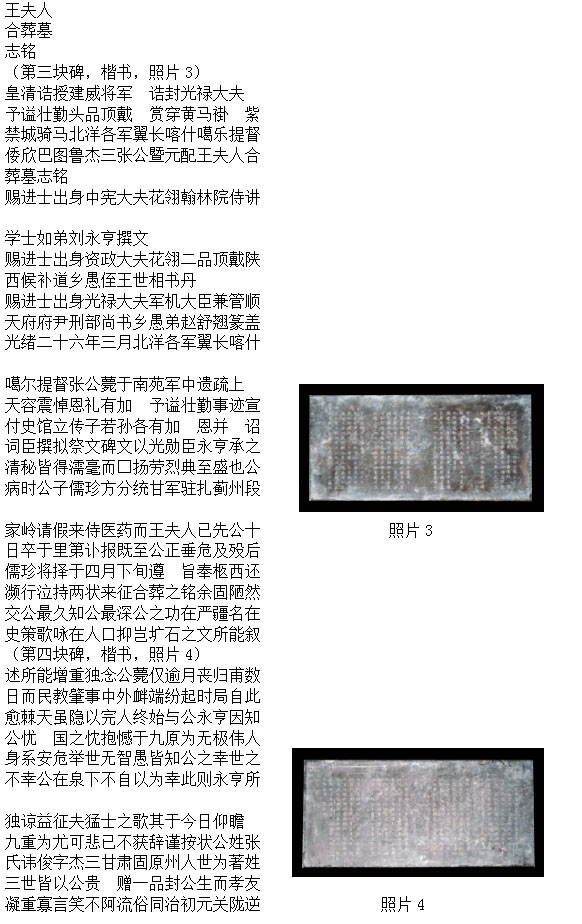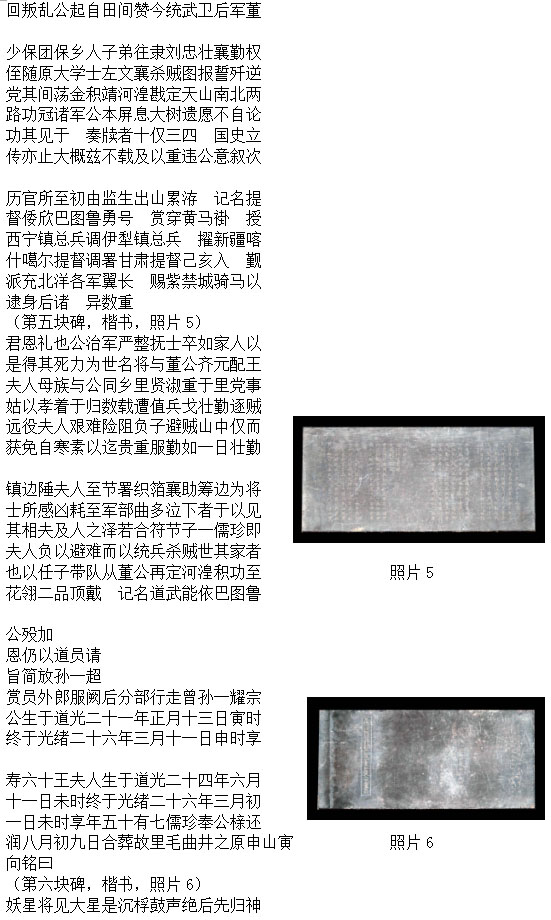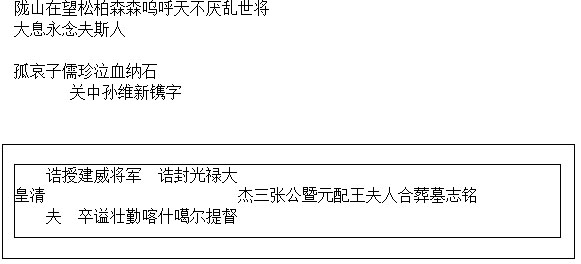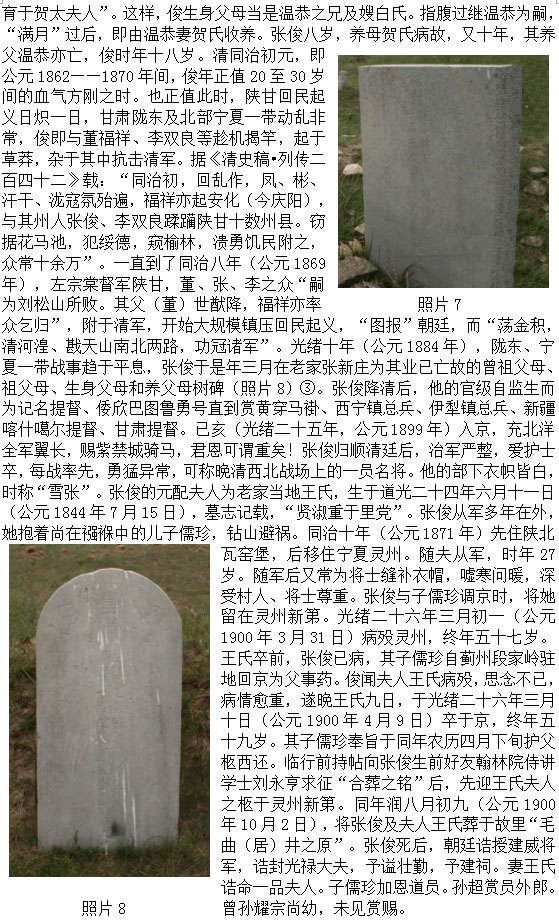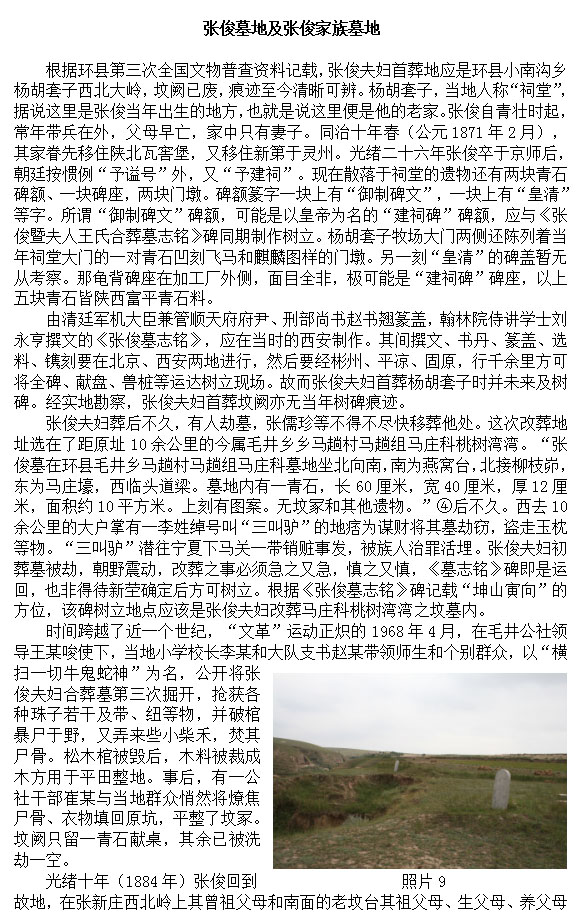《张俊暨元配王夫人合葬墓志铭》(简称《张俊墓志铭》), 现收藏于环县博物馆。为青石质,共六块,长74厘米,宽35厘米,厚24厘米,周边光素无纹饰。前两块墓志(即志盖),篆书阴刻“皇清诰授建威将军诰封光禄大夫予谥壮勤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北洋各军翼长喀什噶尔提督倭欣巴图鲁杰三张公暨元配王夫人合葬墓志铭”64字;后四块墓志(即志石),楷书阴刻,计1132字。墓志书法上佳,词艺精研,镌刻工致,堪称清代墓志中的精品。此墓志虽然署名合葬墓,但志文内容基本以张俊为主,通篇溢美褒扬之词,详尽记载了张俊生平事略,简述了王夫人及子孙后代等情况。现将志文抄录并考释如下(志文均以简体字释出,六行为一段,格式如志文):
志主张俊,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十三日,卒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初一日,享年五十九岁,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清史稿》有传。
“俊,字杰三。金积堡之役,与福祥并授都司。规西宁,余虎恩困峡口,俊力战解之。连破小峡、润家沟,从攻河州、肃州,以战功历迁至副将,赐号倭兴巴图鲁。光绪初,从征西陲,复乌鲁木齐,擢总兵。锦棠令入关募军,於是成定远三营。先后从克东西四城,晋提督。安夷复叛,俊倡议主剿,众论譁起,锦棠独韪之。寇窜库伦,俊追至木吉,分三路入,战良久,手刃执红旗悍卒,寇愕走。进至卡拉阿提,会日已入,止舍。天未曙,整军复进,日午及之。寇不能反拒,枪矛所至,尸相填藉。抵黑子拉提、达坂,止馀数十骑,逾山入俄境,不复追。是役,四昼夜驰八百馀里,凡擒爱伊德尔呼里二人,安夷所谓“大通哈”也,胖色提以下数十人,犹华言“营官”。赐头品服、黄马褂,授西宁镇总兵,调伊犁。二十一年,代福祥为喀什噶尔提督。寻还甘肃。二十五年,入都,充武卫全军翼长,兼统中军。逾年卒,谥壮勤,予建祠。俊好舞刀,所部衣帜皆白色,时称“雪张”云。”(《清史稿•卷四百五十五•列传二百四十二》)①
《清史稿》与墓志记载基本相吻合。一般来说,墓志志文的内容往往是不加篡改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它所记载志主生平行历、迁官次第、氏族世系等,比史传要详实可靠,而史传中的人物履历,往往择其大者、要者,微者、小者略去不载,作为真实记载死者生平事略的文字实物—墓志,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它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墓主的基本情况,这对于研究一定历史时期人物生平活动则不可或缺,另外,史书与墓志记载的内容往往有些地方不尽相同,将这些互异的记载相互对比,有助于断定正误,用来纠正彼此的谬误。
志主身世及履历
志主张俊,字杰三,甘肃固原州人(清属固原州毛曲井,现属环县小南沟乡),“世为著姓,三世皆以公贵,赠一品”。 据现存环县小南沟乡杨胡套子张俊养父母碑载(照片7)②,他的父亲“姓张氏,讳温恭,叔恪其字,先世晋人,一迁庆阳董志原,再迁固原毛居井”。如此看来,张俊的祖籍应是山西。该碑还记载,俊父温恭“年已壮,冢嗣未立,贺太夫人(温恭妻)恒引为忧。嫂氏白(夫人)指腹语之曰:‘若生男,当告夫子为叔嗣’。及生果男,即杰三军门也。阅月遂
共树碑四块,皆保存完好。唯其养父温恭、养母贺氏碑背面有记事碑文,其余只有正面镌刻某某之墓文。
墓地占地约3000平方米,墓碑有两处。一处有张俊为父母、叔父及祖父母各立青石墓碑一通,父母墓碑有碑座(已残破)碑头。其叔父母、祖父母碑均为碑头碑一体。正面有碑文,另有青石桌面一块,桌裙一块,香炉两个,栓马桩两个。以北200米处有张俊为曾祖父母立碑一通,正面有文字,碑座及香炉各一块(照片9)。
根据以上墓碑和《张俊墓志铭》文,又经当地访察,可知张俊过继叔温恭后,仍为单传。堂兄弟共五人,即榜、仲、萃、俊、仁。同支堂兄弟四人,即榜、仲、仁、俊。张俊生一子儒珍。当时有两侄。即宝珍、怀珍,又有一孙名斌。斌是否与张俊殁时《墓志铭》中所记的“孙超”为同一人,不得而知。《墓志铭》还记载当时张俊有一曾孙名耀宗。关于张俊的嫡系后裔,至此尚未见记述。张新庄一带,现时张姓颇多,或言不同姓,或言与张俊同宗,但代序含混。张俊死后,他的独生子儒珍仍在外当差,且有灵州新第,其子孙散居宁夏等地,亦未可知。⑤
张俊墓志涉及到晚清时期的众多史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纵观张俊的一生,他与镇压回民起义、平息新疆叛乱等清末大事件密不可分,现笔者对该墓志中所反映的几个事件考释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 甘肃回民起义
清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发生了回民起义。当时,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攻入汉中,陕西回民纷纷响应,起义军以大荔的王阁村和羌白镇为主要据点,控制了渭河两岸,并屡次围攻省城西安。同治二年,陕西回民起义遭受清军的残酷镇压后,分两路先后进入甘肃境内:北路经乾州(今乾县)、邠州(今彬县)、长武,驻扎在甘肃固原、华亭一带;南路由凤翔经汧阳、陇州,活动在清水、张家川等地。陕西回民起义进入甘肃境内后,引发了甘肃回民反清起义的浪潮。回民起义军相继攻占了固原、平凉、狄道、宁夏、灵州等地。同治五年春,数万陕西回民起义军因粮食短缺,大举返陕。在陕西边境华亭县的上关、下关、尖骨山及马峡口一带受到清军的堵截阻击后,大部遂经平凉、泾州向庆阳府转移,集结在董志塬,号称“董志十八营”。
董志塬地处甘肃东部,隶属于庆阳府,位于蒲河与马莲河之间,南北长约280里,东西宽约150里,“介居环、庆、泾、原、邠、宁之间,为秦陇要膂”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陕西回民起义军在董志塬,按照原来的村社分住各村镇,每支起义军的驻营地称营,共有十八个营地,总称之为十八营。十八营设元帅,有马正和、白彦虎、余彦禄、崔伟、陈琳、禹得彦、冯君福、马长顺、杨文治、马正刚、马生彦、毕大才、阎兴春、蓝明泰、哈连金、邹保和、张代雨、马维骧等。十八营在组织和活动上仍然保留了原来的分散性,但各营之间相互协作和共同作战,彼此联系,已形成了一支统一的抗清武装力量。“董志十八营”控制范围大致“北到安化(今庆城县)的驿马关,南到宁州(今宁县)的丘家寨,西到镇原的肖金镇,东到合水县的西华池”⑦,给陕甘清军以极大威胁与打击。
随着斗争的发展,甘肃回民起义相继形成四股较大的势力:宁夏金积堡马化龙部、甘肃河州(今临夏一带)马占鳌部、青海西宁马文义部、甘肃肃州(今酒泉一带)马文禄部。清政府先后派胜保、多隆阿前往镇压,均未奏效。继派杨岳斌围剿也以失败告终。北方一时形成了“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的“捻回合势” ⑧的局面,出现了西北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高潮。
二、“董字三营”的设立
同治初,关陇爆发了回民起义,安化县、环县团勇于环县、固原一带被回民军攻破,几于覆灭。董福祥、张俊、李双良等联络各路乡勇民团以拒回军,招兵买马,扩充实力,队伍发展到数万人,辗转于陇东、陕北一带,与清军抗争。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福祥部众已发展到20余万。董自封为“陕甘自卫总团大元帅”,张俊被任命为元帅,兼任军师。他与董福祥在陕北抗清期间,为建立根据地,筹集粮饷,扩充兵源,出谋划策,竭尽全力,密切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善谋”的才华初露头角,深得福祥赏识。七月,清军开始对陕北实行大规模围剿。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遂调湘军刘松山部,率军围攻董福祥、张俊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十二月,清军刘松山部向董军根据地陕北大举进攻,董军不支,后退至黄河沿线。在前有黄河阻拦,后有大军追逼的形势下,董、张遂于十二月二十四日降清。刘松山征得左宗棠同意,挑选董部精壮4000余人,编为“董字三营”, 董福祥领中营,张俊领左营,李双良领右营。随刘松山镇压回民起义,深得刘松山及其侄刘锦棠器重。
三、镇压回民起义
同治五年(1866年),陕甘回民起义进入高潮,清政府慌忙授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的大权,旋又授予钦差大臣关防,使其全权从事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活动。同年十一月,左宗棠集军政财权于一身,起身赴任陕甘总督。他向朝廷提出了处理陕甘问题“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战略构想:“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主,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可免中梗之患”,⑨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左宗棠把西北问题看做一个整体,分三步来解决,即先剿捻军,再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最后出关收复新疆。
为了实现第一步进兵计划,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首先从董志塬开始。在左宗棠大军层层围困的重压下,回民起义军难以抵挡清军的进攻,伤亡很大。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二十五日,清军占领庆阳。左宗棠向清政府报告说:“统计是役杀毙、饿毙之贼,及坠崖而死者,实不下二三万人。……积年蚁穴,搜荡一空,贼之精骑悍党,销亡殆半。”⑾可见起义军损失是相当惨重的。失掉董志塬后,陕西回民起义军残部只有分别依附于甘肃的四大据点。这年五月,左宗棠移驻泾川,步步为营,向西推进,依次展开了对甘肃回民起义军四个据点的进攻。
同治八年(1869年),全国和陕甘的形式已发生了重大转折。一方面,清政府在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后已可腾出手来扑灭陕甘回民起义的烈火;另一方面是随着全国斗争形式的逆转,陕甘回民起义的高潮已经低落。为此,左宗棠确立了一个分路进兵的计划:北路由刘松山由绥远、花马池直指灵州金积堡;南路由周开锡统陇南诸军由秦州取道巩昌(今陇西)进攻河州;中路由左宗棠与刘典督军从陕甘大路入甘,回民起义军形势更加孤立。
在与回民起义军作战中,清军每攻破一个堡寨,“寨内贼匪……悉行歼毙”,“斩杀净尽,逸出者无几,生擒者,立即斩决”。在这样严酷的镇压下,金积堡回民首领马化龙领导的回民起义军,在强大的攻势面前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并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十四日,刘松山在马五寨被起义军击毙。左宗棠任命刘松山侄刘锦棠统帅湘军,更加穷凶极恶地对金积堡实行围攻。而董字三营“从攻金积堡,福祥袭卡后,被创不少卻,破其礼拜寺。顿板桥,寇来争,与萧章开夹击败之,金积堡平,超授都司。”⑿十一月,金积堡弹尽粮绝,十六日,马化龙亲赴刘锦棠营中求降。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十三日,马化龙被凌迟处死,金积堡失陷。同治十一年(1872年),“从刘锦棠至碾伯,趋峡口,与陕回禹得彦、雀三大战,破之。进击白彦虎於高家堡,焚其垒而还。”⒀“规西宁,余虎恩困峡口,俊力战解之。连破小峡、润家沟,从攻河州、肃州,以战功历迁至副将,赐号倭兴巴图鲁。”⒁从1868年算起,共计五年,董福祥、张俊协助左宗棠完成了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任务。
四、平息新疆叛乱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西汉年间,中国的文献中已把此地称作西域。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 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西汉政权曾两次派张骞通西域。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 年),西汉政府又命郑吉为西域都护,遂设都护府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及至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 年)开始勘定西域,四年后将西域改名新疆。清政府在伊犁(今伊宁市)设伊犁将军,为新疆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另设乌鲁木齐都统,为该地区的军政长官,地位仅次于伊犁将军。乌鲁木齐以东设镇西府和迪化州,由镇迪道统辖地方民政事务,隶属于陕甘总督。新疆回部事务,则设立伯克管理,伯克由清政府任命。
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和各种矛盾的激化,人民日益反抗清政府的统治。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期间,全国许多地区的起义纷起响应,同治三年(1864 年),新疆各族人民也先后在库车、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举行起义,打击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但起义的成果却被各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所据有,新疆地区出现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即以喀什噶尔(今喀什市)为中心的金相印、司迪克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得璘(妥明)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政权;以和阗为中心的玛福迪、哈比布拉汗政权;以伊犁为中心的迈孜木杂特政权。这些割据政权的混战,给伺机入侵新疆的外国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 年1 月),位于我国新疆西面的浩罕汗国利用金相印、司迪克向其求援的机会,派阿古柏带领侵略军进入新疆,先后攻下天山南路的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县)、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县),和阗(今和田县)等地。同治六年(1867 年)又攻占乌什、阿克苏和库车。阿古柏在喀什噶尔悍然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意即七城汗国),自立为汗,据有南疆。同治九年(1870 年),阿古柏势力又向天山北路扩展,在北疆打败妥得璘政权,占取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新疆几乎沦为异域。
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翌年,张俊随董福祥率甘军出关,向天山北路进军。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张俊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所向披糜,连克木里河、古牧地、乌鲁木齐。在围攻玛纳斯城的战斗中,清军受阻,他受命率部在城北挖地道、掘长壕,用炸药轰倒城墙,终于攻克了此城。在收复南疆的战役中,他受命募兵组成“定远三营”,自为一军,独立作战,一举攻克南疆门户达坂城,活捉沙俄傀儡阿古柏的大总管爱伊达尔呼里。接着挥师急驰,穷追不舍,攻克托克逊城。八月,收复喀拉沙尔、库尔勒、库车、拜城等地。回民军白彦虎、伯克虎率残部西逃,后入俄境,投靠沙俄。是年二月,攻占和阗,擒斩守将金相印。至此,南疆八城全部收复。新疆重归祖国版图。在收复新疆战役中,张俊浴血奋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清廷赏穿黄马褂、头品顶带、褒花翎,授西宁镇总兵,后调任伊犁镇总兵。
光绪十年(1884 年)九月三十日,清政府在新疆正式设省,以刘锦棠为首任巡抚。从此,新疆与祖国的联系更加密切。(15)
结束语
张俊虽然积极参与了镇压回民起义军的作战,有段不光彩的历史。但是,他指挥清军收复和保卫了新疆,这一重大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在作战中所表现的不畏强敌、敢打敢拼、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沉着机智、灵活机动、出奇制胜的指挥才能,在晚清反对外敌入侵的作战中也是不多见的。在刘锦棠建碑勒名的6名将领中,张俊为其中之一。史载:“文襄(左宗棠号)削平陇右,恢复新疆,什(十)九赖甘军力。而福祥之立功,则又皆俊所左右,公论昭然,不可掩也”。(16)
在他这些经历中“荡金积,靖河湟,戡定天山南北两路”,尽管史料中对此记载丰富翔实,但是志主的经历对深入研究这些事件和清朝末年的政治、军事仍具有一定的价值,尤其对于环县地方史研究具有重要的补证作用。
此文章发表于《陇右文博》 2014年 第二期